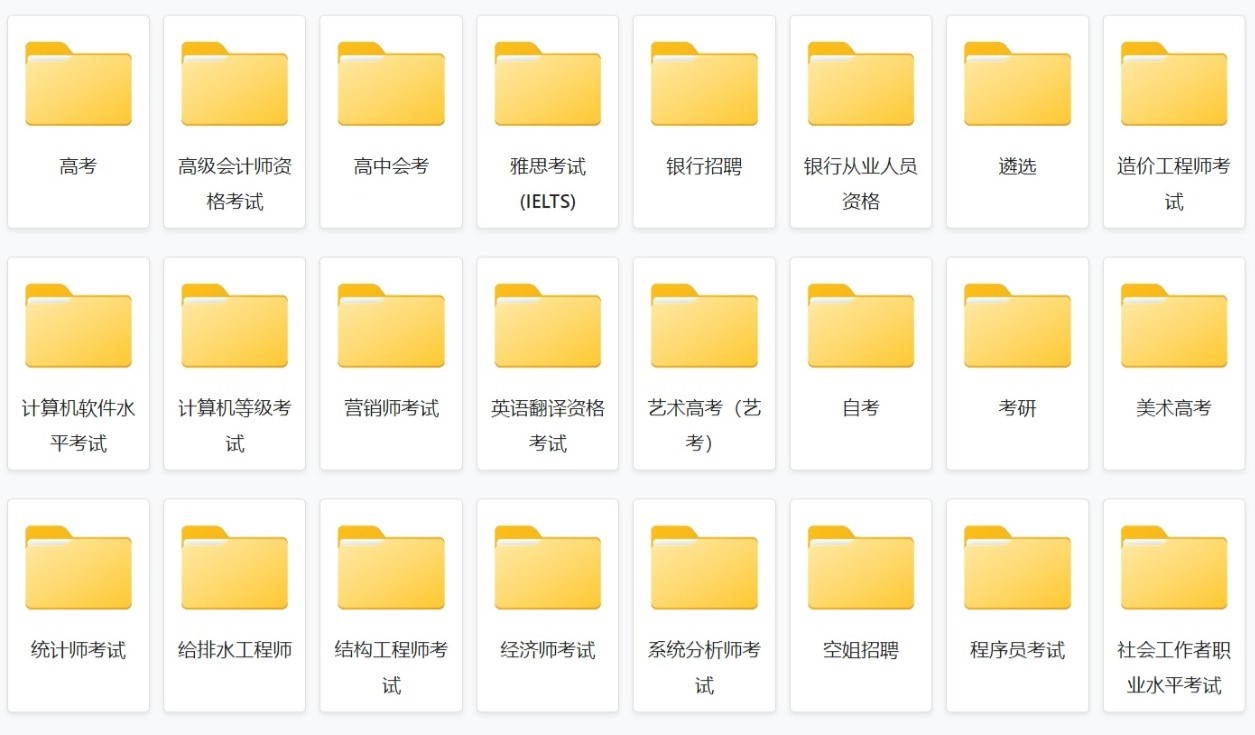材料分析题
地方性写作是一个视角,无名或隐名的写作也是一个视角。早在前几年,我们就后者进行过讨论,我们认为后者支撑起了一种“泛文学”的写作。人们早就应该注意到,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写作潜能。市场经济又使得每个人获得了文学的权利,表达意识的觉醒使大众有了交流与自我表现的欲望,而技术最终使这一切得以实现。技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即以写作而言,正是因为技术支持下的新兴媒体才催生出新的写作形态如博喜、电子杂志微博和微信等等。在现实中,文学几乎以日常生活的样态存在着,只不过在现代发表体制看来,它们并不是文学罢了。而如今,计算机、网络、移动终端,电视互动等系列新媒体,将这些自然的、自在的、丰富多样的文学呈现出来了,将其从匿名状态中彰显出来。它们与传统的出版或发表方式虽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所呈现的内容已经不是私人性的了,它们同样进入了与他者的交流.进入了公共领域。不仅是内容,还有文体。我肯经在一-次散文研讨会上说,不要再囿于传统的散文文体了。实不仅是在散文,在所有文学研究与讨论中,总以为有一个标准的不变的文学。 当我们讨论文学时,往往都是以经典作品、文学史标准为标高的,虽然对文学-直缺乏自然科学一样的定义和标准,但依然存在大体相似的模糊认同,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同样影响着对文学的看法、判断和评价。实文学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类似于生命形态的存在,是个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交叉的进化体。它一直处在变化与进化之中,从横向上看,文学存在不同的样态,如类型和文体,而且不断出现新的样态。从纵向上看,存在不同阶段的文学生命体,从不自觉的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朴素的文学到精致的文学,从简单的文学到复杂的文学,而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其不可否定的本体性的意义。许多人文学科都具有相似的情形,如社会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等,但人们常常用现代学术体制的标准将其提纯,归一,本质化,定型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危害很大。比如散文,从横向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散文文体,记事、抒情、写人议论等。还可以另行区分。如艺术散文、杂文纪实作品等。纵向维度则可以区分不同的层面。从纯艺术的创作散文到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这中间的层级很多。我们不能因为散文家们的创作散文就否定了普通人日常表达
的价值。比如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微信,我们不妨称那些原创的微信为“微散文”或“微文”,微信圈有大有小,但-则原创微文哪怕只感动了几个人甚至-个人,我们都不能无视它的价值。一位微友这样说:“你有怎样的朋友园,你就有着怎样的微信。总是传播着吃了,喝了,...这也是一群朋友。”她这样说自己的微信阅读体验:“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我很少说话。人与人的交往,有时是不需要说话的。不是吗?我只是阅读,只是学习,只是用自己的心灵感知着太多美...对于手机,对于微信,我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它简直就是我的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如何能不喜欢?”(李云《微信,另一种阅读》,文艺报》2014年6月11日)村上春树曾经叙述过日常生活中许多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他简称为“小确幸”,文学之于人有太多这样的关系与状态,我们不能因经典带给,人们巨大的感动就否认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字所给予的微小而确切的幸福,这已经关系到文学的人道主义了.事实上,在我们固守的传统文体以外,文学的边缘或模糊地带已经越来越广阔,文学泛化的局面已经形成。这种局面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化时代的到来,美化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重要表征与生活方式,它渗透到各个领域,“修辞” 成为每一个人工产品的必要工序,即使在实用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不断更新的、追求极致与唯美的艺术设计,只有美化与实用功能高度结合才能得到大众的接受。日常生活审美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文字是美化程度最高的方面,它已经全方位改变了今日的语文世界。我们的一切文字表达无不在如何美化上努力,广告、招聘、求职、策划书、纪实报道、即时新闻,以及几乎所有的文字出版物。连同原先严格规整的人文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表达都莫不如此。在当今.人们可以在更多的空间进入文学的氛围,也可以从更多的媒介和更多的文字作品中获得文学生活的满足。(参见笔者《无边的文学》)
但这一切又确实很少进入专业的文学研究领域,也常常不入所谓纯文学作家们的法眼。究其原因,应该是文学专业化带来的结果。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些,而不是相反,像一些理论仍然在做的一样,或者视当今的文学现实状况于不顾,或者以自为过时的理论和立场强作解人。不可否认,古代的文人文化,现在的知识分子文化都对俗文化、对大众文化抱有成见甚至敌意。除了美学趣味上的分歧之外,可能还有对权力、地位与利益的占有欲和对这些可能失去的恐惧。约翰凯里早就认为,白教育普及化和报刊业兴盛后,读写不再是精英的特权,特别是报刊培养出了市民趣味后,知识分子被冷落了,”大众报纸构成了- 种威胁,因为它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 ,完全忽视知识分子, 并使他们成为多余的人。”(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于是,知识分子心生怨气,产生了对大众与大众文化的普遍仇恨:“梦想大众将灭绝或绝育,或者否认大众是真正的人,这都是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虚构的避难方法。更激烈、更实际的避难方法则是如下的建议:阻止大众学习阅读,以使知识分子重新控制用文字方式记录的文化。”(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当他们不可能阻止大众文化时,只能大写作的复杂度,从而将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并运用自己在教育、制度与学术上的话语权贬低大众文化。造成后者的自卑,以达到保存自己的脸面与利益的目的。事实上,专业与职业的文学并不只是因为其审美优势而获得地位,许多非文学的因素- -直是文学的支撑力量, 所谓“纯文学”就一直没有纯过,各种权力和利益一直是文学的潜在或显在的影响力。而文学也参与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文学与非文学是相对的。我觉得本质主义要不得,但历史主义却是需要的。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都认为,文学从书写物中独立分离出来是文学的进步文学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写作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其这一历史非常短,更长的历史是文学与其他书泻不分彼此地共存共荣。而且,当你想当然地以为文学已经独立时,其实文学在文学以外顽强地生长着。是历史地、变化地看待文学,还是以现代文学体制下的文学观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我主张前者。前几年我就呼吁要重视埃伦迪萨纳亚克有关“书写过度”的理论。迪萨纳亚克从她的物种主义美学立场出发,认为人类本来建立在自在状态的审美关系到后来被打破了,艺术变成了一柱越来越艰难的事情 ,她在乔治迪基和阿瑟丹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由批评家商人画廊拥有者、博物馆的董事、馆长、艺术杂志编辑等组成的一个艺术界,是为一些事物与对象赋予“艺术作品”的地位的策源地。艺术家们创作的东西是“欣赏的候选物”只有艺术界买了它们,卖了它们,书写展示了它们,它们才能被确证为“艺术”。至少从现代主义美学发生起,广义的批评家们的过度书写越来越严重地将艺术从人们的现实中分离出去,乐此不疲地无限夸大艺术与生活的对立与差异。艺术的含义并不是靠普通人的认知被感受,而需要通过专业人士的阐发才得以揭明,艺术接受成了越来越高深而专业的工作。而艺术家们被这套编织得日趋严密的权力体制束缚钳制,只能拼命按照这样戒律的旨意凌空蹈虛,殚精竭虑地强化作品的非经验化,非现实化,这是另一极的过度书写。两极的过度书写相互激荡攀升,导致艺术与人本越来越远。
这一过程也可以描述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包括中国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状况。为什么当时曾有理论批评的空前繁荣?为什么有如火如荼的先锋文学运动?为什么又有了理论制造创作的说法?这便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相当典型的两极书写过度按迪萨纳亚克的阐释,过度书写导致同时也加剧了语言-符号崇拜现象,这种现象到了后现代主义那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利斯·米勒就说:“不存在先于语言的在世界和时间中生存的经验’之类的东西。我们的一切“‘经验’都被语言渗得透之又透。”(转引自(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从来不可能抵近或到达一个没有经过中介的现实。在我们与我们对不用言词而占有意义的向往之间存在着无法改变的、不可通越的问隐、裂缝和断裂。结合永远被延迟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延异存在于我们和其他一切之间”((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经过后现代主义阶段,“由识字促成的客观性和无根性现在变成完全的隔断和不在场”((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这样的描述与中国曾经流行的理论是多么的相似。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理论最简洁的表达就是“语言即现实”,“语言即本体”,它从素绪尔有关所指与能指关系的理论出发,尽可能地夸大能指的地位,将文学描述为-种在能指层面自由滑行的符号活动。文学成了断线的风筝,它脱离了大地,在无限的天空任意飞翔。于是,专注于形式,专注于创作者对语言的感受,营构- -座座语言的迷富,写作成了个人的不及物的游戏,技术的探索,演进与积累被解释成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而文学与艺术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迪萨纳亚克指出,艺术要比识字历史久远得多,“艺术是表达、表现和强化一个群体最深层信仰和关切的仪式庆典的永恒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群体意义的载体和群体一心一意的激励者,与仪式结合在一起的艺术是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传统社会中,为‘生活的艺术’而非为艺术的艺术才是通则”。“艺术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和必需的行为,就像其他普通又普通的人类职业和使人专注的事情,如交谈、工作、锻炼、游戏、社会化、学习、爱与关心一样,应该在每个人身上得到认识鼓励和发展。”((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我们现行的文学体制、理论体系,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对此难道不应该反思?“过度书写” 提醒我们警惕被我们拼命维护的文学形态对文学的伤害。已经说不清有多少年了, 人们一直在这样的形态下表达文学的审美经验,有许多抽象出来的标准和要求,用以评判、区别文学与非文学,来决定怎样的书写者是作家,而其他就不是.包括文体、修辞、表现方法、语言风格等,都被整合进相对固定的方式将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格式化,通过长期的反复的教育来训练人的感觉,通过文学史指定的作品将人的阅读圈在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文学理论与批评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正如迪萨纳亚克所论述的那样,“当书写和理论创造了 艺术这个概念用艺术这个标签来为所赏识的候选者命名并以此构成艺术时.那些书写和理论化的人本身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些概念和标签,好像概念和标签是重要的界定特点,是艺术的本质”((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如果明白这些,再跳出圈外去看看民间与基层的文学现实,就不会再死抱着那些概念和标准不放了。
行文到此,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客观地描述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中蓬勃的文学生态,二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学生态长期被忽视的原因略作分析。毫无疑问,我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的文学存在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问题,也不意味它们无需反思。实际上,在这方面确实需要警惕民粹主义与反智倾向。也就是这些年的调查和观察,我以为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存在着不少令人忧虑的状况。
当我们为海量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所欣喜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我不是在所谓文学质量上来衡量他们的写作,而首先是在价值层面上表达我的遗憾。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如今的情形是,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救...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场人文灾难。如果揆诸历史,民间常常守护着传统的价值,或者会提出新价值观,但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确缺少这样的力量与动因。这在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宣泄式、怨对式甚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而事实上,嘉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如前所述,我之所以强调民间写作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它们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路径,但恰恰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地方抑或是无名或隐名写作,都还不能说能够担此重任。
(摘编自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